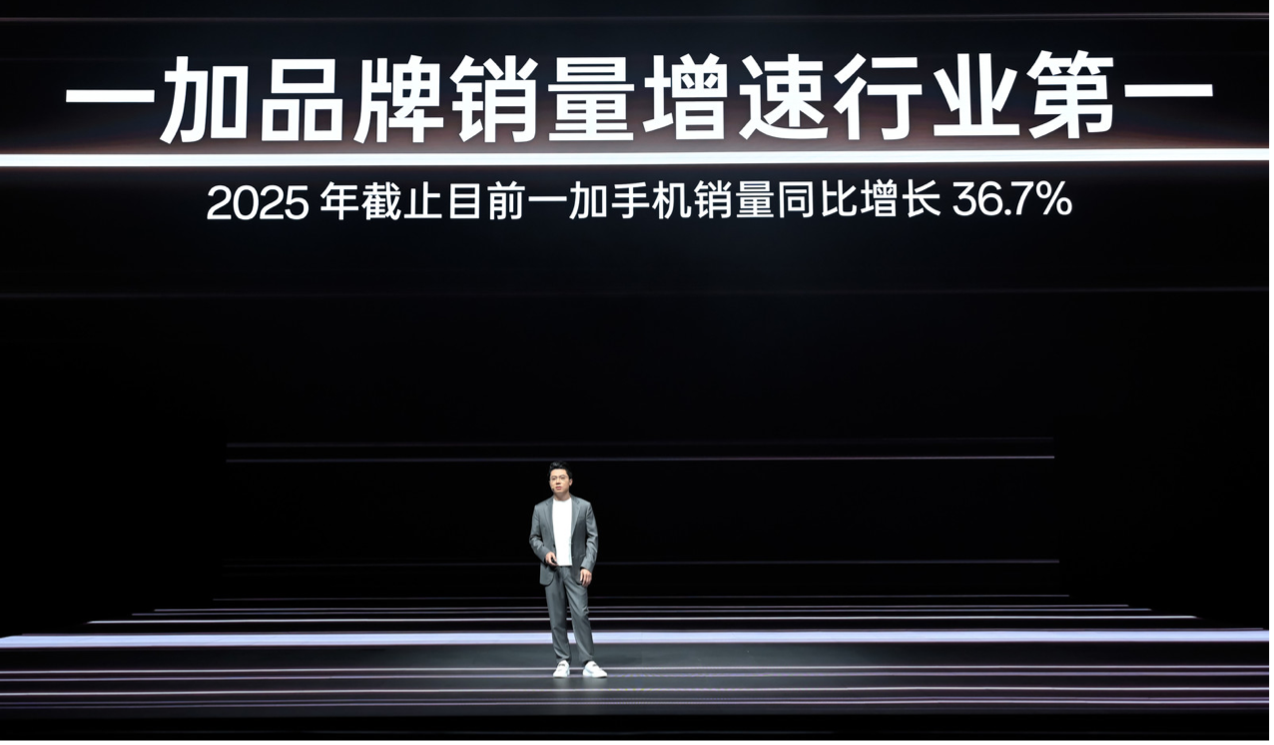近日,一篇名為《教書四十年,被學生罵到痛哭》的文章在教師圈里悄然流傳。那位勤懇一生的老教師,在學生一句不堪入耳的辱罵聲中尊嚴落地的畫面,像一根細刺,扎進了許多人的心里。
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故事的開始,只是一頁未完成的作業。老教師在班上平靜地說:“作業是為自己,不是為我;今天有人沒交,我不追要,但希望大家自己算清這筆賬。”這話輕得像一聲嘆息,卻引來了驚雷。一名男生猛然起身,踢開凳子,將課本狠狠摔在地上,手指幾乎要點到老師鼻尖,隨之而來的國罵,讓老教師四十年的師道尊嚴碎了一地,回到辦公室痛哭失聲。
那位老師在文章里寫下的比喻,久久縈繞在我心頭:“我們像蒙著眼罩的驢,學生咒罵的鞭子抽過來只能兜圈拉磨,還要自己嚼碎所有委屈。”這哪里是比喻,分明是成千上萬教育工作者的生存寫照。
那個站起來辱罵老師的男生,在辦公室里緊握雙拳,眼淚橫流地嘶吼:“我媽我爸天天冤枉我!”“我不需要任何人管我!”這些話語背后,是一個在家庭關系中受傷,繼而將戾氣投向教室每一個角落的靈魂。他的叛逆,不過是從家庭戰場轉移到學校陣地的延續。
而另一個場景同樣讓人窒息。那個在物理課上公然嗑瓜子的女生,被班主任要求背誦課文時,抓起語文書,然后“啪”地一聲摔在地上,又跺了兩腳,留下一句完整的國罵揚長而去。更讓人心寒的是電話那頭家長的聲音:“老師,她要敢罵你,你就大耳刮子呼她!出了事我擔著。”
這句“大耳刮子”,在空氣中凝固成最冰冷的諷刺。女家長看似慷慨地賦予了權力,實則精妙地推卸了責任。這句話的潛臺詞是:你動手,我支持;但后果,你獨自承擔。它讓教師站在了懸崖邊上——動手,萬劫不復;不動手,威嚴掃地。
我們的教育,似乎走進了一個怪圈:當孩子在家里沒有得到恰當的管束,到了學校就會變成無法無天的“刺頭”。家長在品德塑造上“甩手”不管,卻在學業成績上不斷“越界”施壓。那些本該在家庭中建立的行為邊界、敬畏之心,缺失的部分最終都在教室里爆發出來。
規則并非不存在。《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》白紙黑字,但有多少學校敢于真正使用?當頂格處罰不過是“回家反思一周”,這種不痛不癢的懲戒,如何能觸動那些早已麻木的心靈?
在這片教育困境中,我們需要的不是另一篇充滿術語的分析報告,而是找回教育最本真的東西——尊嚴,不是教師單方面的威嚴,而是知識、規則和人格應有的尊重。
或許可以嘗試讓“教室的歸教室,家庭的歸家庭”。比如,在每學期的家長會上,不再是老師單向的匯報,而是共同觀看一段記錄孩子成長的短片,讓家長看見那個在集體中不同于家庭的身影。班主任每周可以給家長發去一條不涉及成績的“成長快報”:今天誰主動擦了三遍黑板,誰在同學難過時默默遞上了紙巾。讓教育的光芒,先照亮這些被忽視的角落。
更重要的是,我們需要看見每一個“問題學生”背后的哭泣。那個罵人的男生,他的憤怒源于何處?那個嗑瓜子的女生,她的不屑又來自哪里?有時,一個學生在放學后被班主任留下,不是因為批評,而是因為一句“我看得出你最近很不開心,想聊聊嗎?”
那位老師在文章結尾處寫下的心聲,或許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暗夜中前行的微光:“我們心寒于一個學生的惡語,但終究是為了更多學生那句無聲的‘老師好’。”
教育之道,或許就在于——即使被現實所傷,依然選擇為那些純凈的眼睛而堅守。
畢竟,當一本教科書被摔在地上,我們每個人都能聽見那聲沉重的回響。那不僅是一本書落地的聲音,也是某種東西在我們心里破碎的聲音。
(圖源網絡,侵聯刪)